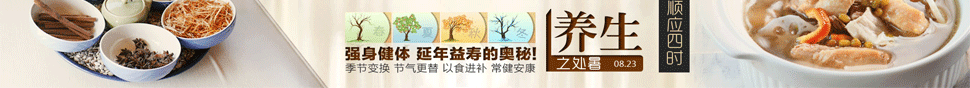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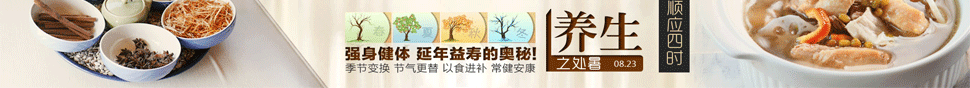
原创顾有容物种日历
自有文明以来,人们开始系统化地认识植物,都是为了把它们当做资源来利用。人类花了几千年时间尝试,最终发现,能生产淀粉、蛋白质、脂肪和纤维、用于满足温饱需求的植物种类很少。剩下那么多种植物能用来干啥呢?治病。
是医生还是植物学家在各种文明的传统医学中,植物都是药材的主要来源。因此,最早记录大量植物物种的文献几乎都是药典,或者叫本草书;早期的医生和植物学家这两种职业人群的重合度也非常高,以至于本草学现在被当做植物学的前身。我们想要了解人类认识某种植物的历史,很多时候得去查阅古代的本草书,物种日历的作者们一定对此深有体会。
提到记录大量植物物种的药典,自然不得不提李老师和他的《本草纲目》。比较不同文明的本草学文献中对同一种植物用途的记载有何异同,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。不过,植物分布有其地域差异性,能拿来做这种对比的,至少得是欧亚大陆温带广布的物种。
鉴于我们生活在一个传统医学尚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国度,“某种植物的药用价值国人很熟悉,但洋人不知道”的情况相当常见。但反过来,中外皆有分布、被洋人当药材用了几千年、中国人却不太当回事的植物似乎很少,我能想到的一个例子就是缬(xié)草。
缬草的花序。图片:pixabay染一抹粉红缬草(Valerianaofficinalis)的分布遍及亚洲、欧洲的温带和寒带地区,并且在北美大量引种栽培。在中国,从东北到西南、海拔~米的广大地域都有缬草生长;然而,历朝历代的本草书里都找不到“缬草”这个名字。
在古文里,“缬”字和植物联系在一起时,都是用来描述芍药或者山茶的花色,诸如“红缬子、白缬子、湖缬”等,形容深浅不等的红色斑点和条纹。这很贴切,因为“缬”字的一个涵义就是红晕,特别是醉酒后脸上的红晕。
缬草的花略带粉红。图片:Jeffdelonge/wikimedia把“缬”和“草”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并用来指代一种植物的是日本人。缬草在日本也有分布,开花时一片深粉红色的花蕾中夹杂着浅粉红色的花朵,很像当地的一种扎染工艺“鹿子染”(“鹿の子絞り”或“鹿の子染め”,染出的效果像梅花鹿背上的斑点)的效果。因此,日本人称这种植物为“鹿子草”(鹿の子草),将它的根部入药时,则用了更加文雅的名字“纈草”(けっそう),也作“吉草”(きっそう)。
中文“缬”字的本义就是扎染,“以丝缚缯染之,解丝成文曰缬也”(唐·玄应《一切经音义》),而“缬草”这个名字,是近代随着西学东渐,从日本的植物学文献传入中国的。
鹿子染的衣物。图片:thehipp.org猫主子也爱吃其实中国的本草书记载过缬草属的植物,只不过用的不是这个名字,而是“马蹄香”和“蜘蛛香”。
“马蹄香”见于《滇南本草》:“马蹄香,一名鬼见愁。形似小牛舌,叶根黑”,从有限的描述和流传至今的地方用药来看,这里指的是蜘蛛香(Valerianajatamansi)这种植物,也叫心叶缬草。
在今天,马蹄香是马兜铃科Saruma属植物的名称,这个属是细辛属Asarum的近亲,连拉丁名都是把后者开头的a挪到词尾变成的。蜘蛛香有个俗名是土细辛,这并非巧合,反倒说明了在没有分类学的年代,这些心形叶、根有香气的植物非常容易混淆。
缬草的叶(左)和蜘蛛香的叶(右)。图片:RandyNonenmacher/wikimedia;MuhammadAdnan/EthnobotanyResearchandApplications()“蜘蛛香”这个名称最早见于《本草纲目》,李时珍难得地原创了一条名词解释:“蜘蛛香,出蜀西茂州松潘山中,草根也。黑色有粗须,状如蜘蛛及本、芎,气味芳香,彼人亦重之。或云猫喜食之。”
估计李老师这次是问对了人,没有自己拍脑袋,对蜘蛛香的产地(西南山地)、形态(根长得像藁gǎo本、川芎xiōng)都做了正确的记载,还埋下了猫主子也喜欢吃的小彩蛋——这居然是真的!不过,蜘蛛香毕竟不是什么重要的药材,李时珍这寥寥数笔之后,别的医家也没怎么
本文编辑:佚名
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://www.madoulinga.com/mdlzz/12283.html

